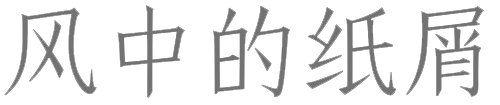一
衰败的泥土香,无预兆涌入,像石子丢在平静的海面上,香味的涟漪,从脑部荡漾开,似乎传到心脏、脊柱、指尖……不存在之物。淡黄色的火焰在跳动,编织成网,成团,要将我淹没。但不是火焰,而是光,冲破湿软泥土,找到我残破的脸庞,肆意窥探、嘲笑。不!不!不要看我丑陋的模样,请收起目光!我要闭上眼睛,它却纹丝不动,粗糙雕刻的眼睛早已硬化,勇敢的与光明对峙,但我害怕,想抱住下潜的根系,一同埋入深处,土壤的深处。一阵污泥的臭味突然炸开,大脑蠕动,试图逃离这场酷刑,但那阵香味呢?香味躲藏在光明里,越来越亮,越来越亮!一只手,挖开我面上的泥土,多么粗糙,多么温柔!每一次挖掘都是音符,穿过密布的根系钻入耳中,陶醉,陶醉……直到我迷失在炫目的辉光中。一个黑影,长发,贴近了我的面部,长发钻入土壤抱紧了我的头部,一阵阵抖动,似乎是某一种动物?我仔细思索,蛇?光线划过黑影的侧脸,青黑色鳞片犹如窗花透射着神圣的光芒,左脸轻轻贴在我的右边的脸庞上——若是那破碎的表皮还能称之为脸庞的话。她轻轻的呼吸,我幻想着呼吸的热量,裹挟着香气在我面旁氤氲,再撞上她冰冷的皮肤,凝成香味的水珠从脖颈滑落,滑落,浇灌我塞满泥土的口腔。
青黑色鳞片轻微抖动了几下,我用眼角余光瞥见她正在闭上的双唇,我错过了她的低语。土壤能否记住她说的话,那被浸湿的泥土,却无力接住下落的言语,越来越深,掉落到不可测的黑暗深渊,我费尽全力,一,二,三,她说了三个字,究竟是什么呢?
她已经离去。

能再说一遍吗?三个字,第一个是“w”开头,第二个完全没有印象,第三个呢?“i”音结尾,“我”和“你”?词库,需要词库,在地上,沿着侵入的根系向上攀爬,穿过中央大道,来到第五区的图书馆,寻找三个亲密的字词,然后,然后呢?编写一首诗,藏在身体的各个角落,等到她下一次再来,她会来吗?她会来的,我满心希望。我的思绪满满堆在喉舌尖,等她冰冷的脸庞再度贴近我,诗从嘴中乌黑的土壤缝隙钻出,爬上青黑色鳞片,渗入她的皮肤,耳尖,嘴唇……
可我做不到。
身体微微颤抖,一种奇特的力量在我体内流淌,细不可闻,却又无法阻挡。我将意识慢慢收回到颅内,一步一步的抽离,然后我看见了遍布体内的菌丝,繁复却有序,把我破碎的身躯紧紧的锁住——即使那只是一团团没有意义的粘土,谁会在乎灵俑的身体是什么组成的?只要它能站起来跑动就行。菌丝在我体内以不可察觉的速度蔓延,很慢,但那股力量却如涌入海洋的江流势不可挡(后续找一个符合拉尼卡环境的比喻)。菌丝的起源埋藏在我难以企及的深处,于我身体的一部分自成整体,是我的血管、脊柱、大脑、神经。我忽然意识到,我的知觉,意识,体验都在沿着菌丝游动,传递到我身体的每一个角落,像在五线谱上跳舞的音符,时不时还会有来自泥土、花系的杂音涌现。
静静的躺在墓园深处,再无一人来临。菌丝使我全身都束缚在土壤中,我成了它的一部分。芒草摇曳,那从远处倾泻而来的天光,是许久未见的太阳,还是一群疯子制造的白色脉冲灯?水滴悄悄记录逝去的时间,上一次我还在第四区随同公会成员训练,然后巨大的木桩横扫而来,我和我的灵俑兄弟们变成东一块西一块,接着是欢呼声、咒骂声、以及逝去的阳光。都说死亡是生命的归途,可我从未活过,自然谈不上死亡。我究竟是什么时候有意识的呢?在第一次粉碎之前?或许没有,无意义的往事刻在大脑里面,菌丝唤醒意识之后,我再将所有的记忆一点点吞下,聊以消遣。总有一天,我身体的每一处都会知晓曾经发生了什么,可那些并不重要了,不是吗?我的第一天,是与她相遇的今天,我的诞生,我的新生,我的存在,于这一天开始。而后的每一天,都是今天的扩展、延申、往复、叠加。
我能做到。我尽力想着,试图把拒绝、否认的音符推走,那不是我的意识,是杂音聚集形成的恐惧。
我听到菌丝聚集在左手掌中交谈、密谋,但睡意试图把我掩埋,意识的潮水追不上菌丝的尽头,在编织成网的三岔路口,迷失,迷失……
二
“在寂静的旷野,把深爱的他一口一口的搅碎,和我体内的每一个细胞结合,然后,结成花朵。”在葛加理和植物待太久,人总会变得不正常。依稀记得这是某个真菌共生体朗诵的爱情诗歌,她在我眼前一口一口吃下逝去的爱人——所以有时候诗歌里恐怖的比喻、象征未必不是真的。
“我的爱,是严肃的律法,崇高的喷泉,不灭的阳炎,请收下吧!它永不消逝!”这段话写在某个泥潭里腐烂的铭牌上,大抵是律法公会士兵所作,也只有他们会写出爱如律法这样令人作呕的比喻了,要是他们的爱真如律法,那也一定是漏洞百出的主条例后面加上一堆说不明白的附加条例。
休息之后,脑内的菌丝更为紧绷,离散的思绪开始汇聚。诗歌从记忆海岸的深处被推到岸边,我试图寻找可用的信息,为她作诗。现在岸边浮现的都是不可用的废弃垃圾,都说诗人的灵感来自梦中,混乱的梦海里有取不尽的素材,如果能做梦……
沉重的喘息闯入,夹杂着混乱的脚步声。
鲜红的她,艳丽的她,被鲜血浇灌的她。蛇形的头发凌乱不堪,有几根“头发“——蛇发的头已经断掉,暗色血液浸满白肉。她的皮甲上满是锐利的刀痕,一场凶恶的战斗,蛇发女妖通常都是刺客,要么一刀割断目标的头,要么被对方割断,这是爆发了正面冲突吗?
她搀扶着坚硬的藤蔓,来到我的旁边,缓缓躺下。伴随着清晰可闻的吸气声,肾上腺素的作用早已消失,冰冷的汗水卷着冰冷的血液流进冰冷的土壤,咸腥味沿着菌丝冲来,体内升起一阵疼痛的幻觉。她还能撑住吗?我还未知晓她的名字……

“芳瑞卡。”
她的名字是芳瑞卡,可这并不是我的想法,谁在说话?
“啊,我真是受够了这个一直在自我意淫的蠢蛋——好吧,蠢蛋也算是在说我自己。但是每天浸在无可制止的幻想中,还嘟囔着什么俗气、乏味、酸臭到作呕的诗歌,你真的不累吗?“
我在自言自语,脑海中,但那又不是我,从菌丝的另一端传来,他的声音傲慢,狂放,毫不讲礼貌……
“你他妈说谁没礼貌啊?现在的小孩都这么没有教养吗?连上前线战死的战士都不懂得尊重,要是我手上有鱼叉,一定要让你体会一下什么叫做最严厉的教训。哎,说起我当年进入葛加理先锋队的时光啊,那可真是不容易……“
太吵了,我选择了一条受影响较小的菌丝,感知着聒噪的回响,爬过大脑凹凸不平的沟壑,在另一端我找了一团陌生的聚合体,腐败的绿色,时不时的抖动,像一个激情的演说家,我慢慢靠近,并到主菌丝上。
“喂喂喂,你在干什么?”
接入。
红的、绿的、黑的记忆片段一一闪过,我看见芳瑞卡拿着精美的匕首像切菜一样卸掉我的头颅,我的老板在房间内大喊大叫却无人理会。接着看到我像垃圾一样被丢在墓园的灵俑旁,芳瑞卡挖了些土把我埋好。最后我看到菌丝缓缓延申,裹住还未腐烂的螳螂尸体,将其一片片切碎,拽到我的身体里。
“在寂静的旷野,把深爱的他一口一口的搅碎……”我想起今天捡到的诗篇。我试图探索更深处的地方,但被一阵强劲的思绪挤了出来。
杰德,刻洛族守卫,昨天被她杀害,丢进墓园,在菌丝的作用下和我结为一体。
“能不能不要说的那么暧昧,和你结为一体?”确实,我们还没有真正的结合,菌丝还没能完全渗入他的脑内,我还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他——更何况我连自己都不是很了解。
“哇喔,看看这一对乳房,真是圣品……”我将意识转移到外界,芳瑞卡已经卸下了着身的皮甲,正在脱贴身的内衣,饱满而富有弹性的乳房轻跳而出,我不由得一阵脸红。“美味,那玩意一定很美味,想想看,久经锻炼的蛇发女妖乳房,充盈着力量、鲜血,能有几人能够品尝到,听说她们交媾之后就会把对方吃掉,作为饲养孩子的养料。”
那不是螳螂才有的习俗吗?
“虽然我们刻洛族人有一部分长得像螳螂,但严格来说,我们并不算螳螂。要知道我家婆娘都换过五个男人了,我是第五个,嗯,这么说,马上就要第六个了,新来的家伙不一定能够伺候好她,我那时候可是干的我婆娘几天都下不了地……可惜我们必须去做该死的护卫,护卫啊,护卫啊,护不了自己,也护不了别人。不过被芳瑞卡这样鼎鼎有名的蛇发妖杀掉也值得了,蛇发妖下死,做鬼也风流,要不说我现在还能近距离观赏她,你瞧瞧她的脖子,繁密的细鳞若是亲吻一定别有风味,再探上她冷酷无情的脸庞,我敢打赌,吻住她嘴唇的时候,兴奋的蛇发会从你的头部把你狠狠包住,体验致命的窒息快感!知道什么皮肤颜色最棒吗,白色?俗气柔弱,黄色?一股臭水沟的味道,显然是蓝黑色的皮肤,冰冷的血液在皮肤下翻滚,当你用充满着热量的皮肤抱住她时,便能感受到热量从自己体内被抽离的交互感,她狠狠的剥夺你的一切,血液越来越兴奋,再接着就是灵魂纠缠在一起,狂热的倾诉彼此的爱意,再说说她们的腰……我操他妈的!“
我几乎要再次睡着了,杰德大吼又把我惊醒,发生什么事了?芳瑞卡的腹部有一道深红的刀口,我心一紧,差点忘记她正处于生命危险中。
“你可别自作多情了,这点伤算不上什么。他妈的,完美的躯体,究竟是谁,伤害到了她!不对,这是好事,要是我……要是我就好了……伤害蛇发妖的人才能征服她们,无法伤害的她们的只会被征服……“
就像你一样被丢在黑土里无人问津。
“狗崽子,你他妈在一天之前还是个只会胡思乱想的恋爱脑,现在就变得如此尖酸刻薄了?“有许多不属于我的记忆想法滴落下来,水滴石穿,从菌丝蚕食掉杰德的那一刻起,我就已经开始改变,等到杰德被菌丝全面侵入,他也会改变,我们合为一体,变成全新的我。知晓到这一点后,我只有一点点的慌张,新的我还会继续想着她吗?
“太肤浅了,喜欢一个女人——蛇发妖,你要做的就是找一张桌子,把她按在桌子上,脱掉裤子——两个人都要脱掉,如果是裙子也可以不脱,然后做你该做的事情。“
我肯定不会这么做。
“你会的。“
我不会
“我会。”
沉默。芳瑞卡已经清洗好了腹部的伤口,正在用匕首切掉坏死的蛇发,平时看上去可怖的蛇发现在显得安静无比,等待匕首的裁决。芳瑞卡,我并不了解她,她是谁,她从哪里来,她做什么,喜欢什么,统统不知情。
“蛇发女妖一族,只会生出女性,生很多,丢在阴暗的地下室,让她们自己厮杀,最后活下来的成为公会女王的御用刺客。芳瑞卡,则是其中的顶级刺客。”
灵俑通常和士兵一起训练,难怪说以前我从没有见过蛇发妖。
“至于她们做的那些工作嘛,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,政治阴谋、叛变、谋杀、黑吃黑、封口、处理残迹……拉尼卡底下没新鲜事,这话你总听说过吧?”
拉尼卡,确实没有太多新鲜事,发生的故事总是耳熟能详。酒馆里面大家不关心俄佐立颁布了什么新律法,更关心伊捷那只老龙的私生子在哪,又或者是拉尔总督在哪和他的小情人约会。葛加理公会更是被人忽视的地方,住在这里的居民多多少少都会患上植物性神经紊乱,自言自语,莫名其妙,就像我这般。
杰德没有说话——菌丝上感受不到他的动静。我注意到芳瑞卡在盯着我看,盯着我的下半身。我简直不敢相信,杰德鼓动着下体的菌丝,包裹着一堆土壤冲破了灵俑表皮,堆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性器官!妈的,灵俑也会有性器官吗?我怎么爆粗口了?但我肯定灵俑的那玩意不会长这样,刻洛族的也不会长这样。
“别他妈挑三拣四了,能整出来就不错了,还真指望我做一个巨魔屌给你?”
他非常自豪。我无法理解他对于干蛇发女妖这件事情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执念。“好好看看吧,芳瑞卡眼中的欲火,已经按耐不住了,她肯定巴不得立马坐上来。”
不,是你的欲火按耐不住了,下体的菌丝有节奏的颤抖着。芳瑞卡的眼神依旧冰冷无言,杰德你最好不要总是待在那里的菌丝上,我担心她一刀把你切掉。她早己穿好了皮甲,但比起裸体的姿态,皮甲勾勒出的身形更加诱人。
“你总算意识到了,如果你连她的身体都不喜欢,那你的爱就是一坨虚假不可信的巨魔排泄物,我操!他妈的!轻点!”
芳瑞卡的匕首轻轻拂过小土柱的上沿,我是说,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称呼那玩意。菌丝柱?擎天柱?还是土具?芳瑞卡蹲了下来,简单观摩了一会儿菌丝柱,然后开始用匕首尖在上面雕画,她随性的握着匕首,但走线精准平稳,毫不犹豫,就如同真正的绘画大师。我能听到杰德的嚎叫,夹杂着痛苦、快乐、癫狂以及一堆说不出的情绪,即使是远远躲在另一端的我也能感受到复杂情绪带来的快感,菌丝引诱着前往快乐之地,我不敢迈步。
“操,快点来!我要起飞了!“
我相信他真的能起飞。芳瑞卡停下了匕首,她雕了一条蛇,从根部缠绕着菌丝柱,长着巨口,试图吞掉柱子顶端。难不成她还是一个隐藏的艺术家?
“她是个完美的婊——“
快点去死吧,杰德。兴许是听到了我的呼唤,芳瑞卡挥起匕首,一刀切掉了菌丝柱。杰德激动的嚎叫戛然而止。
芳瑞卡转身离去,我轻轻咀嚼,这才是她的模样,我见到了。墓园亦归于寂静,杰德依旧没有说话,被切断的思绪应该还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,我打算再去聚合体里面看看——没有多久后就是我自己的了。
三
“真疼啊,那娘们下手真够狠……不过也值了,我真是嗨到爆炸,你没来真是可惜了。”
正如我所料,杰德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吹嘘自己的杰作和奇妙体验,但我此刻看着他,不免感到一阵悲哀,狂热的兴奋下原来是……
“你他妈在想些什么?那可是他妈的用匕首的交媾!比口交更爽,更刺激!你在他妈的悲哀个什么劲?真他妈扫兴的玩意,哎,想到以后还要和你这种啥也没体验过的雏待上好几年,我都要晕了,可怜我家老娘们会不会怀念我的大家伙呢?”
撒谎。
“你说什么?”
你是个骗子,你才是那个无可救药,沉浸在自我意淫中的人!好吧,也算不上人……
“你他妈的……”杰德顿了顿,“你他妈看到了?你他妈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进去看了!你他妈凭什么?凭什么!”
这是我的脑子,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!杰德突然扑了上来,他的意识凶狠无比,把我踢到菌丝的边缘,狠狠的噎住我,我感觉我的意识上下左右都在碎裂,被他撞得七零八落,好在我很熟悉菌丝网络,我挑着很少有意识经过的小道,绕开了杰德的追捕,他太粗心了,注意不到这些阴暗的角落,我偷偷躲着看他在主菌丝上狂怒,自我拉扯,嘶吼,哀嚎,然后变成悲凉的哭泣。他已是强弩之末。
“你想要什么?”
我什么也不想要,我只想被公正的对待。但我紧紧收住了自己的想法,他听不到。
“对,你都看到了。我就是个废物,好吧,没有那玩意的废物。”
杰德在一次护卫行动中失去了性器官,其实我不是很懂刻洛族的性器官是什么样子,总而言之,五年前他就没有办法进行性行为了,神经上传来的快感也无法释放,一直活在扭曲的压抑里面。
“婆娘也跟别的男人跑了,她怎么能不跑呢?”
从来就没有找过五个男人的老婆,也从没有让老婆爽上一晚上。这不过都是他的臆想。
“但是这他妈的能怪我吗?老板说好了结束后给我安排移植手术,可他妈的他最后偷偷把名额给了他的小儿子,还不知道是谁生的小儿子!他让我再等几年,呵,谁他妈信呢?”
找了很多医生,要不就是没有合适的移植体,要不就是手术费用高的吓人,就凭着当护卫的微薄薪水,根本不够用。
“你觉得我很卑贱?我只是在做我一直想做的事情!你觉得你对她的爱很高贵很神圣很了不起?”
我从没这么觉得……糟糕,声音太大了。
“他奶奶的,我看你往哪跑!”杰德又追了上来。
你纠缠我也没有意义,那些东西迟早有一天我都会看到的!我他妈的让你看了吗?老子正他妈爽着,就你他妈事多!我只是想确认一件事。你想确认什么?确认我是不是在骗你?我想确认你对她的感觉……
杰德停了下来,似乎在认真思考。
“她让我快乐了,让我感受到再一次做男人的尊严,以后有机会,我要真正的干她。“
“你满意了吗?“
我开始想念鸡肝菌酿造的美酒,或许只有口腹之欲才能熬过今天的漫漫长夜……

四
我早早醒来,已经想好了诗歌的内容,迫不及待的想要读给芳瑞卡听。但我还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喉部,嘴里面也满是黑土,恐怕想让她听到没那么简单。你可以写给她。我们已经忘记了昨天的争吵。我可没忘记,不过不重要,男人只有在争吵和斗殴里面才能成长,算了,说了你也不懂,把诗的内容给我,我可以给你写到屌上去……我拒绝,首先不提那玩意被砍掉了,其次让我在性器官上写一首诗?有什么不好意思的,她昨天还在上面画画了?你没感受到?你写诗,她画画,多浪漫啊,呵呵呵……笑的真难听,我可以把诗写在肚子上,那里空间比较大,或者写在手上,如果给出一朵玫瑰,太浪漫了。呸!这也叫浪漫?你要么用鸡儿让她爽飞天,要么告诉她你的一片真心……你说的没错,杰德,我们应该把它写在胸口上,爱意从我的心中涌出,她一定会感受到的!
“我的爱,比菌丝还要辽阔,还要缓慢。“确定是这一句没有要修改的地方了?嗯,或许不用说这么直白,我的爱,可以用一个比喻或者象征……我给你个建议,我的屌,比大树还要崇高,还要坚挺,一定能吸引她的注意力。好吧,这么一说我觉得还是不用改了。不懂风情的家伙,我要开始了,别吵到我。
不得不说,杰德确实有天赋,在操控菌丝这一方面,他很轻易的就能拉扯着菌丝在体内游走,寻找合适的地方破土而出——比如昨天的小玩意。一点都不小。现在他鼓出我胸口的表皮,缓慢的走出字符的线条,日思夜想的诗句,终要交给她,我忐忑不安。
搞定,我得去休息一会。说好了,下次我做大屌的时候你不能阻止。好的好的,下次,下次我就是这里的老大了,那时候你想做什么还不是我做主?
冷冽的芳香缭过鼻尖,她来了。
但不是一个人,她穿着美丽的裙子,身后还有一个,带着面具的人。妖精祭师,怎么,没见过,一群神神叨叨的家伙,没有人会喜欢他们。妖精啊妖精,生的俊俏可人,即使搁着面具也能看到他那暗灰色的迷人脸庞,身形优雅挺拔,眼神锐利又挑逗,站在她身旁的是妖精,而不是我!我听说妖精的屌都会特别大,和巨魔有得一拼,等下可以好好看看。杰德,你不是认真的吧,巨魔?马上就要上演一出交媾好戏了,他妈的,老子也想加入。
我却不忍直视,静静地躺着,听着菌丝在体内抖动,听着她和他的呼吸,听着风声如涛,初阳奔涌,黑水浮动,我似乎已经睡觉,渺远空间里面嘈杂声四起,墓园缓慢归于沉寂,死亡的声音不断游走……
别睡了!出事了!
我骤然清醒,然后看到,鲜红的她,艳丽的她,被鲜血浇灌的她。妖精握着匕首,她的捂着自己的喉咙,血涌如泉。
他杀了她!
他杀了芳瑞卡!可这有什么奇怪的,拉尼卡底下无新鲜事,她是一个刺客,背叛和被背叛是注定会遇到的。可她今天穿着裙子,她本该开心的跳舞,开心的和他交媾,开心的读我写的诗,她不该在今天死去。
妖精把她拖到我的面前:“抱歉啊,我也不想这么做的,但是你知道,芳瑞卡,做这一行不是轻易说退出就能退出的,新来的那个姑娘能力也很不错,培养一下应该比你更出色,并且她不像你,有不切实际的幻想。“
妖精抓着芳瑞卡,她面对着我,不时有血液溅到我的脸上,胸口上。她面露痛苦,蛇发挣扎撕咬,妖精却不为所动。
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,画画,写诗这些对一个刺客来说,确实有点多余了,不是吗?“
你懂什么!我愤怒的吼叫。
“这是你写的诗吗?’我的爱,比菌丝还要辽阔,还要缓慢。’哈哈哈,真有趣,你就陪着你的诗好好睡一觉吧,别醒来哦!“说完,妖精扔下芳瑞卡,她趴在我的胸口上,嘴中吐出血沫。
“我……“她在说什么。
“的……爱……“她在读我写的诗,在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“比……比……“可她已经没有力气了,鲜血染红了诗句,她把手搭在胸口上用菌丝隆起的句子上,停止了呼吸。
我放佛看见了她的笑。
她……那个传奇杀手芳瑞卡,死……了?

五
我步入漫长的回廊,黑暗寂静无声。老师曾经说我们可以抵达的尺度,是无穷尽的,上到繁星的轨迹,下到地脉的根茎。
现在的地方既不像童年训练的地下室,那个地方充斥着血腥味,汗臭味,还有失禁的粪便味。这里有一股清香,陌生却又熟悉的清香,完成任务后我经常去的墓园就有这个味道。
墓园……墓园……
前面有光,我径直走出去,一个刻洛族,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,还有一个长得像灵佣的家伙,有点羞涩?
你的心上人一来就骂我,我们以后真的要跟她在一起吗?
芳瑞卡,我……我等了你好久……
我也走了很久,久到快忘了我自己是谁。
那一天,我们刚刚相遇的时候,你说的三个字是什么?
我突然想起来一切,那三个字是——
——完